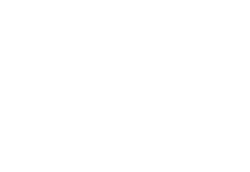岑允逸先前打算將這個展覽命名為《健兒》,我想到的則是《奧運寫真》。「是《奥运写真》嗎?」他馬上通過網上的MSN問道。後來我們跟光影作坊的孫樹坤討論,結果就敲定了現在的題目。
有關中文正體字和簡體字的議論,也許可以為今趟展覽做個註腳。我瀏覽互聯網上一些中文網站的時候,久不久就會看到有用簡體字發出的留言,要求別人使用簡體字;相反在簡體字的網站裡,我卻從未見過有留言者要求改用正體字的。目前的政治環境之下,簡體字是主流、正體字屬於邊緣,是大家都清楚不過的事。近年來許多人都把正體字改稱為「繁體字」,明顯的就是要讓簡體字奠立成為正統的意思。
只是對於原本不是使用簡體字的香港人來說,「繁體字」雖然筆劃較為繁多,寫起來也比較緩慢甚至麻煩(隨著電腦流行和中文輸入法的改善,這個問題其實已經得到解決),但始終是中國語文的正統,而且字義分明,字形也更好看。我有幾位可以深交的國內朋友,他們基本上也認同我們的看法;然而當我問到他們是否願意改用「繁體字」時,他們卻一致表示不大可能。說穿了,這裡牽涉了兩個權力的矛盾,一個是政治上的,一個是文化上的。
再進一步說,簡體字代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續漸發展出來的一套很壞的語言表達方法,以及好些其他華語地區人士都未能輕易接受、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價值觀與生活模式。香港有位高水平的作者陳雲最近出版了一本名為《中文解毒》的書,裡面就說了不少中共式的語言為本地的中文和社會帶來的不良影響。
香港至今仍然不是使用簡體字的地區,它的居民的生活模式也跟國內人民有相當大的差別。而且這裡流行的口頭語是廣東話,對於中共官方語言的普通話,大多數香港人不是不懂,就是說得不很流利。當然,自從一九九七年香港的宗主國轉變了之後,彼此的距離確是逐漸拉得比較接近了,但要完全融合,我看除了增加溝通相互了解之外,還要在文化和文明程度方面多下功夫才成。
岑允逸近年進行的攝影計劃,都是觀察中國在急遽發展之下社會面貌呈示的微妙變化。去年他就出版了個人專集《係 • 唔係樂園》,描述大陸各地許多新興的公園裡出現,在外來人眼中很覺得奇異的景物。值得注意的是,岑允逸取景時雖然常帶幽默,卻絕無譏諷輕藐之心:他的鏡頭在批判當前中國在經濟高速狂飆而現代化文明步伐未及趕上的落差的同時,亦每每包含著一種既有距離但又貼近的自我反省態度,很複雜地流露了後九七的香港人的曖昧立場。
這樣複雜的中港文化身份感情,我以為在今趟展覽的照片裡更是來得明顯與深刻:一方面他也是跟那些在體育館外流連的人一樣專程來到北京,但是另一方面對於他們興高采烈的慶祝情緒,他卻只是能夠當個旁觀拍攝的人。在胸前貼上心型的北京奧運貼紙,或是帶上一副有二零零八字樣的墨鏡,對岑允逸來說都不會是毫無心理掙扎的行為。至於北京市內眾多為奧運而新建造的景物,更好像是《係 • 唔係樂園》的續篇,尤其是那幾頭在商場樓頂佇立的長頸鹿、野象和斑馬,真是酷到難以置信。
我想跟岑允逸說:你有很犀利的眼睛。我也想說:那鳥巢運動場外的一家三口,他們臉上掛著不同程度的笑靨,或站或坐在行李之上給你造像的,你還有他們的電郵地址嗎?
黎健強
策展人手記
岑允逸, Dustin,現年37歲,理工大學攝影設計系畢業,有十多年的新聞攝影經驗。去年為了要以自己的角度來觀察這個被譽為史無前例地規模盛大的奧運會,他將一份被其他攝記行家認為是薪優糧準的工作也辭了,自費跑到北京去進行拍攝,創作出《奧運健兒寫真》這個作品。本來他打算在較接近香港東亞運動會的會期才展出這作品,希望可以藉此引起更多的討論,但在光影作坊的邀請之下,他還是提前把這個作品拿出來和大家見面。
這個以北京2008奧運會為主題的作品《奧運健兒寫真》大部份的照片,其實都都是拍攝些從全國各地前來北京支持奧運會的「閒雜人等」,Dustin認為;「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平民,不辭勞苦地趕來北京支持奧運,他們甚至連入場門劵也買不起,但他們仍是在場館外各出奇謀地努力為奧運打氣,他們似乎不會因此而獲得報酬,他們才是真正的『奧運健兒』。」但細心地觀察便會發現Dustin最感興趣其實不是這羣人,而是在一個史無前例地盛大的奧運會前面,潛藏在背後,驅使這羣背景各異的人作出相近行為的種種能量。Dustin以4x5大片幅底片來拍攝並將人像打印成巨大的照片,他希望觀眾能在這個展覽中產生一種與這些「健兒」臉臉相覷的感覺,他並加入了一些裝置,從而引導觀眾們醒覺到影響著班健兒的這種能量,像是萬有引力般無處不在。
Dustin在《奧運健兒寫真》的拍攝手法,驟眼看來和Diane Arbus的風格很相近,都帶點Freak味,但卻可以說是將Diane Arbus的手法反轉過來應用,Diane經常是透過對拍攝過程的操控,從而「誘使」被攝者作出怪異的表情以達至一種近似psychodrama的張力;而Dustin則以新聞攝影一貫的不主動介入過程的手法,來拍攝健兒們似有若無的表情。Diane很多時候都會將背景壓縮至少無可少來讓人物說話;而Dustin則是透過保留與作品主題相呼應的背景來讓人物說話。但整體而言人物在Dustin和Diane的作品中都有一股Freak味。
在回憶整個拍攝過程中對這些人的感覺時Dustin指出,起初他也覺得這些人的行為甚難理解,似乎他們各自在自己所屬的地方都是”misplaced”(錯配)了的人,而他們都發現奧運會才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地方,因為這兒他們都能找到身份的認同,Dustin後來終於意識到這次奧運會早已被政治所騎刧,支持奧運便被鼓吹成天經地義和理所當然的了,在這種氛圍底下『奧運健兒』們無論各自以任何方式去演譯自己對奧運的支持,其實都是希望能藉此來表現達出自己對國家的愛護和認同,而這份對國家認同感似乎又是這一代的中國人所特別渴求的,奧運只是提供了一次最好的機會和藉口而已。但為甚麼人們會如斯希望有一個展示自己愛國情操的機會?而將愛國精神和奧運會劃上等號又是否一種集體的精神錯配?看來都是Dustin希望透過他的這個作品來探討的問題。
Dustin早年的作品都主要是以香港社會的現像作為題材,雖然他對大陸的題材都有興趣,但最初他都像許多人一樣,認為香港人拍攝大陸很難及得上國內的攝影人,甚至害怕以香港人的眼光去看國內的情況很容易給人一種政治不正確的感覺。但後來還是按捺不住而開始了拍攝大陸的題材。當看到德裔攝影師Michael Wolf在香港拍攝到的作品而能獲得良好成績時,他感到一種鼓舞性的作用。在2006年Dustin以一輯在國內多個不同城鎮公園拍攝的照片,參加北京的影像專家見面會,作品被選為最受影像專家感興趣的34份作品之一,系列中部份作品被舊金山現代對術館收藏。至此他才真正肯定自己當初的抉擇,並續繼將這個題材發展下去,在去年7月Dustin將公園系列的照片結集成書,出版了《係唔係樂園》標誌著他在記實攝影創作過程上的一個里程碑。
94年已經入行的岑允逸去年終於離開已從事十多年的新聞攝影,這多少反映了他對這份工作存在著些心結,他認為新聞攝影經常講求視覺衝撃,但拍攝一張出色的新聞照片,當中常常包含一些機會的元素,,所以Dustin認為「好的攝影記者都是機會主義者」。從攝影記者往往就是一個歷史的見証者而不是創造者的這個角度來看,Dustin的判斷是正確的,但卻要指出的是,新聞攝影一如新聞工作的其它組成部份,都是講求對整體社會價值系統的認同、支持、監察、以至改良,新聞工作在政治學上被視為社會「第四權」的角色早已剥奪了它的從業員擁有太強的個人主義色彩。社會的現況、問題、和發展的方向,如果都能透過新聞攝影而能令社會上的每一個成員都「看」得到和「感受」得到,每一個攝記便都會在精神上獲得極大的滿足,每一個攝記最少在他的崗位之上都應擁抱這種價值觀。不過令Dustin最感因擾的就是在工作中經常被要求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做最多的事,他認為這是過分地追求效率而犧牲了攝影的質素和內涵,這可能才是令他離開這個行業的主因,也是值得新聞界以至社會大眾認真反省的地方,到底我們的社會有多重視新聞的質素?
Dustin認為自己一直以來都有些反叛,都希望能創出屬於自己的攝影風格和角度,打從2000年開始他便自費地跑到台灣去先後拍攝三屆的總統大選,他希能培養自己不再單從新聞的角度去觀察這種大型的社會活動,雖然在過程之中他發覺自己很難一下子便完全抛開新聞攝影的思考模式,但至少他看到一些可能性和一條自己該走的路。目前Dustin希望能走出傳統記實攝影的框框,不再以近距離接觸的手法去拍攝一些個人或團體,而用一種抽離的手法,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研究一些社會現象,從而引發讓觀眾對問題背後的社會因素和力量,《奧運健兒寫真》和之前的《係唔係樂園》都是朝著這個方向邁進的嘗試,在芸芸香港有心的記實攝影人當中,不單是流於感物傷懷,而能夠透過作品來揭示社會現象背後的徵兆的人其實不多,岑允逸是當中可貴的一員。
策展人:孫樹坤
攝影展詳情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