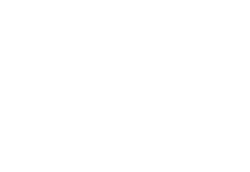單獨 ― 《夜祭》的策展註腳
文:楊陽
中譯:黎健强、楊陽
這 是《夜祭》的策展註腳。就像一般註腳,它是一個文本的延伸;但是,它並非以文字作為依歸,而是屬於展覽的。因此,它留於一個帶著策展性的註脚,關顧著它的 源起 ― 這展覽。這「策展性」跟一般會申明立場和宣佈展覽開幕的「策展聲明」不同 ―《夜祭》並不需要這些 ; 它會自行解說。然而,《夜祭》 仍爲一絲一索的意念與堅執,思想與情緒打開,好讓它要貢獻教育的原意得以維持。真正的教育不在於傳遞指令,而是在於造就有關的事和人最廣闊的發展自我潛力 的空間。在這授與受的意義裡,在這來而有往的流動之中,這個註腳為《夜祭》作伴又結伴,就像光影作坊為《夜祭》作伴又結伴一樣。我並非故作謙遜,只是誠 實。
一、職責所在
或許首先要抗拒將焦點集中於高志强在拍攝些甚麼的慾望,也就是,在某一個意義上,對這些影像宣稱擁有權的慾望。這是困難的,因爲我們這時代,機械自動化使拍攝照片變成一舉即得而非讓記憶沈澱的行爲。高志强的作品的準確性和力量也是困難的另一原因 ― 面對有力的準確性,我們每每急於把它馴服。
能延遲這慾望的話,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就會漲退起來 ― 高志强的作品怎樣達至它們當前的狀況 ― 技巧性、藝術性、政治性、思想性?(至於個人方面,可必須歸於他本身。)
有 天高志强自言自語,說假如蘇珊˙桑塔要寫今天急劇數碼化的攝影 ―《夜祭》也是從這環境鑽出來的― 她會說些甚麼?當桑塔質疑戰爭攝影的暴力程式美學,甚至對紀實攝影的傳統提出全盤批判時,高志强讓紀實與藝術同樣地暴露出來。這是因不能分嚐的內省片刻正 捕逮著單獨的攝影真實。這片刻不是厚待,而是詛咒。如果桑塔顧慮攝影在「旁觀[註一]他人之痛」時被使用為將殘虐自然化的工具言之成理,那麽,當攝影成爲攝影師的同伴,目睹他關注 (旁觀?) 自己的痛楚時,攝影又能否得以再發明?
不要稱這些作品爲「集體回憶」,因爲正如桑塔所說:「嚴格來說,並沒有集體回憶這東西 ― 都屬於集體罪咎感一類的錯誤觀念。但是集體教誨卻是有的。」[註二]。當攝影要尋真理,而不是只求事實,照片就不止於社會所選擇去想的:它們是藝術家的單獨回憶,他選擇將這些回憶曝光時也是要跟它們一起死去;也是說,當那片刻的引力「把作者抽空」[註三],就算是他也無法回來了。
如 果有一種攝影歷史能披露社會以視象不斷作出否定,一種「紀實」之名不足以涵蓋的歷史,那麽高志强的作品就可以(以謙虛的態度)靜靜地和不甘心地(因為他寧 願有其他選擇)擔當一角。面對頽垣敗瓦的世界,一個藝術家還能够做些甚麽?他要令它看來美好易明嗎?還是啞忍無言地等候事情的發生?
引用文學方面的例子,澤巴爾德說:「從被殲滅的世界裡建構美學或僞美學效果的做法,即是要褫奪文學的生存權。」藝術家能够做的不是提供答案或者期望解决,他/她不是去消解,「乃是去揭示衝突。」[註四]某 個意義上,攝影的藝術同樣分擔了這厄劫:那單獨見證的也在宣示他的生存權。所有證供在宣稱擁有真理時都是很準確的。準確性會在甚麽時候變得沉悶呢?這個問 題只有真正的藝術家才會捫心自問。當準確性把他/她的精力抽空時,他/她可以重新開始 ― 謙虛地、誠實地、慢慢地、嚴謹地。
二、逼不得已
當高志强命我策展《夜祭》的時候,我腦海中立刻在「策展」一詞加上引號…